【漫畫介紹】一起搭捷運,好嗎? 第四集(完)
最新消息
不瘋魔,不成活──動畫導演謝文明的步步蛻變
- 2022.12.01
- 漫畫消息
採訪撰文╱張慧慧
攝影╱陳佩芸
轉載自╱文化内容策進院TAICCA
「阿蛾就是我。」謝文明笑靨燦燦。
阿蛾是謝文明在《肉蛾天》(2006)中創造出的苦命女子。這部動畫短片描述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,生在戰亂饑荒時代的阿蛾,一次次地靠賣淫換取死囚的肉身,好讓病重的丈夫與初生的幼嬰溫飽。直到某次她翻山越嶺,珍貴地抱著一條換來的腿,卻迎來丈夫的死訊,且悉心照料的孩子也被偷走,最終,阿蛾沒能撐過她的人生。
這位近年橫掃國際各大獎項的動畫導演,視覺風格強烈,以驚悚的異色奇想出名。而謝文明在碩班畢業前夕揉捏成形的這個角色,帶著他入圍釜山影展、廣島國際動畫影展,標誌他正式踏上動畫創作之路。
謝文明讓纖瘦的阿蛾背負巨大的竹籃,那籃裡放置的不只是她的孩子,更是這名當年將要離開學院保護傘的創作者,內在最深層的焦慮與恐懼,「我那時感覺自己最珍愛的動畫創作就要被結束了,因為迫於現實未來可能無法再創作了。」他把這祕密深埋進這部十二分鐘短片裡,時過境遷,他笑著說:「還好我沒有那麼慘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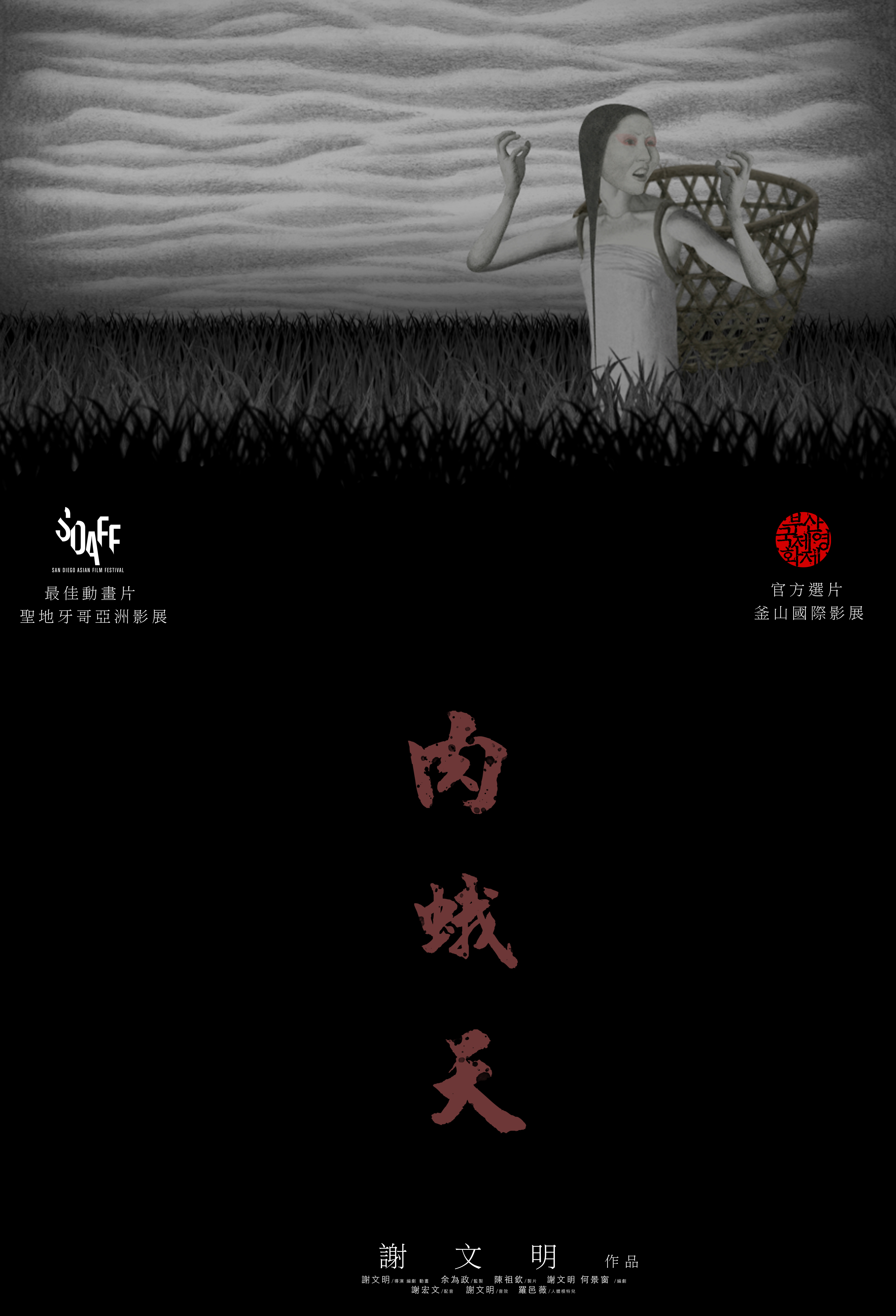
《肉蛾天》海報
炭筆手稿堆疊、擦抹成肉塊之林
謝文明的創作旅途,就外人看來是陽光晴朗,與「慘」字搭不上邊。
自《肉蛾天》開始,謝文明每六年推出一部動畫短片,每回出手,都收獲許多漂亮、驚人的國內外重要大獎。他將這些肯認與鼓勵的獎座,放在自宅客廳靠窗,曬得著陽光的櫥櫃上,也包含最新創作的《夜車》(2020)在這兩年奪得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、全球四大國際動畫影展之一的薩格勒布動畫影展首獎、日舞影展最佳動畫短片。

但他不是那種考高分卻說自己沒讀書的優等生,謝文明是個努力派,欣慰於那些用盡全力搏來的名聲,也不吝嗇表達自己面對創作的一心一意。他相信自己的創作直覺,相信努力會有成果,相信那些國際舞台的掌聲都是戮力而博得的勳章,而時間確實站在他這邊。
「我那時真的很拼!像這個素材,要畫一個禮拜!」謝文明展示畫紙上的一條腿,那是《肉蛾天》中的死囚身體,僅在畫面中出現幾秒,「必須用炭筆把所有物件畫出來。炭筆不像鉛筆,必須花時間把碳粉壓抹在紙上,營造出光影效果跟質感。皮膚、肉塊、肌肉、大腦皺褶等,炭筆都可以描寫得很精細。」他翻閱一張張手稿,像巡視一座王國,為我們細心指路,看每個角色的關節如何拆解,如何重構,如何活動,「很恐怖齁,這些相比鉛筆,要花更多的時間。」
那段時間,謝文明被這個黑暗絕望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,吃不進一口肉,「當時都拍到快得憂鬱症了。」每日清晨五、六點他到早市考察肉攤,也細細觀察2004年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「人體奧妙巡迴展」中200件經塑化處理的器官組織、人體切片與完整大體,就為了那出現在片中幾秒的肉身,也為了更走進那絕望的故事裡。「做每個片子,必須活在那個片子裡,如果沒有那麼進去,你不會做得好。像《霸王別姬》裡程蝶衣的角色,不瘋魔,不成活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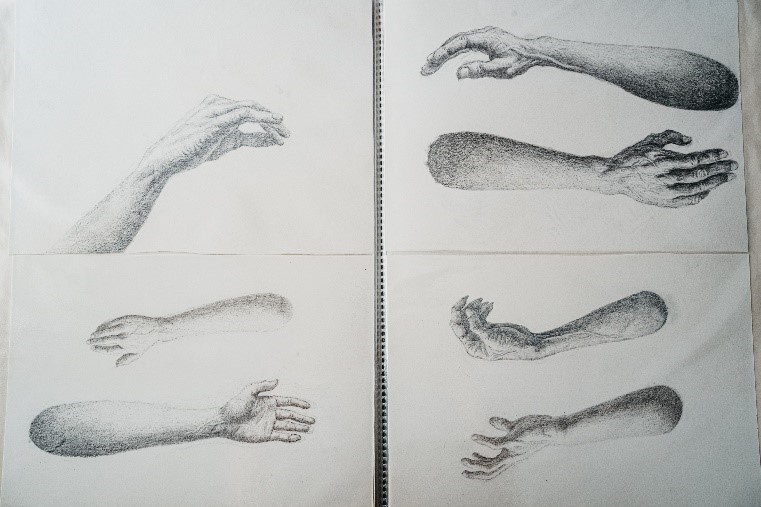
創作最好玩的,是把我的故事講出來
謝文明親和,話不少,訪問初始,他快樂地將一本一本分門別類、收整得齊整的原稿攤開在我們面前,談起每個心愛的作品眼睛放光,雀躍像個孩子,感染力極強,但觸及自己的生活卻總輕巧地閃過許多細節。
我們所知道的,只有這位動畫導演童年時短暫住過新竹那滿布動物、昆蟲的田野;國中時輕而易舉地保送上美術班,因此租了大量的影碟,花了比同齡人更漫長的暑假看恐怖、驚悚片。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電影迷,「高中時我曾想過當電影導演,但由於美術科班出身理所當然念了美術系,其實心中還是非常憧憬電影的。」
那是九○年代,世界秩序正在改變,臺灣也正處於漫長戒嚴解除的頭幾年,各種思潮、藝術類型百花齊放,但卻也是電影產業最沉寂的時刻。
那十年,我國的電影產量從八○年代每年超過百部,到了九○年代雪崩似地從未超過四十部,拷貝數、映演場所幾近全面解封,讓好萊塢八大電影公司完整占據臺灣的版圖,加以輔導金政策,逐漸破壞了臺灣電影的商業運作平衡,使整體產業在惡性循環下趨向萎縮,最低點則落在1999年,本國拍攝長片僅有十一部,輔導金影片就占了六部,國片發行與市場「接近於崩盤」。(註)
懷抱著電影夢的少年謝文明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,進了北藝大美術學院,主修油畫,「我好喜歡這所學校,好自由,每天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藝術表演,有劇場、舞蹈、音樂……都能豐富我創作。」他自白:「當時,我還是走可愛搞笑路線的。」
他從客廳隱藏的系統櫃中,神秘兮兮地拎出三幅畫面朝內,靠牆放著的壓克力顏料畫作,「有沒有很可愛!想不到吧!我學生時期畫的!」其中一幅是頂著法國洛可可風格的灰白假髮,頭頂繞著珍珠項鍊,身穿華服的鹿,被兩隻麻雀掀起了裙子,「《鹿夫人》這幅畫講的是性別。他離家出走,從宮廷跑了出來,因為要追求屬於他的自由。」
「我其實很想講電影可以講的故事,繪畫則比較像是一顆鏡頭的神采。」謝文明拿起母親送給他的一台攝影機,自此開啟剪紙動畫之路,也習慣把自己安插在故事裡,那些訪問中輕巧帶過的生命軌跡,全讓他畫進那些動起來的作品裡,「動畫創作最好玩的,就是能自由把自己想講的故事講出來。」

蒐集東方臉孔的創作者
他確實擅長說自己的故事,繼《肉蛾天》的阿蛾之後,是《禮物》(2012)的孔雀,接著是濱海公路《夜車》上的妻子美蘭。
有意思的是,這些從他自己出發的角色,都有著容易被辨識為「謝文明式」的臉孔,用他的話說,那是「東方」「有味道」「有特色的」臉。翻開《夜車》文件夾,幾頁角色設定貼滿了他從報章雜誌裁剪下的臉孔,「我需要我的演員,所以我會蒐集我覺得適合的臉,蒐集完再幫他們定裝。我隨時隨地都在蒐集,即使是吃碗麵也會觀察周遭人的樣子!」
他所蒐集的臉,不是那些能被輕易喊出名字的漂亮演員或模特兒,都是些沒有太過端正均衡的容貌,但那些不平衡反而給人一種親近感。謝文明從那些臉提煉、創造出的人物,細密地糾纏著幻想故事與他自己的個性,他將虛構與真實,混合在那些用炭筆、鉛筆細膩描繪的肌理中,無法分割開來。

「我都會為角色做身家小傳包括星座……孔雀就是天蠍座的!」這位同為天蠍座的導演笑得很樂。在《禮物》中,孔雀苦命追求雨夜投奔家中經營旅館的已婚男子,過程中,鮮血染紅了她的眼睛,也染紅了整片大海。
這部片的靈感來自日本傳說故事《京鹿子娘道成寺》,啟蒙謝文明動畫創作的日本已故動畫大師川本喜八郎,也曾在1976年的作品《道成寺》改編成偶動畫,片中女子化身大蛇緊追男子,最終殺了他,但謝文明給了截然不同的結局:「我如果是她,我一定會放手,愛錯人,終究還是要放手的。所以她在海中就默默放手了。」
「這個故事吸引我的,是她的執著,為愛往前飛,為了她要的東西認真拼搏。我也一樣,我會為了動畫如此,也算是一種自我投射。」他的作品核心是人,是愛恨癲狂,被恐懼追趕,正在受苦的人,「這些角色吸引我的地方,都是她們執著,不懦弱,有力量,但我最想做的是,覺醒。她們在某一刻意識到自己要改變。所以,孔雀最後放手了, 《夜車》的結尾最後也掙脫了。」
跨國合作,見識到團隊戰力
每部作品,都清楚標示著謝文明在不同階段的改變,「因為要申請補助案,所以從《禮物》開始,我會有很完整的前置作業,一份提案的企畫書,裡面包含分鏡表、文字腳本跟人物場景設計。」他從《肉蛾天》那個站在創作入口正徬徨不安,全憑本能行事的藝術院所學生,成為了一名以藝術為業,務實的工作者,「補助對個人創作很重要,如果資金不到位,很難完成自己想說的故事。」
謝文明說自己「幸運」,幸運生在創作補助資源豐沛的臺灣。九○年代為人詬病的輔導金制度,經過改制後,不斷滾動修正申請辦法,成為新銳創作者的第一桶金與進入藝術市場的敲門磚,「創作者身在台灣是很幸福的,只要你有才華、夠努力,大家會幫你的。我申請到短片輔導金,因而能開啟更完整的動畫之路。」除了《禮物》申請上輔導金,《夜車》也因國藝會動畫短片製作補助與「高雄拍」短片獎助計畫才得以執行。

《禮物 The Present》
他也幸運總是在對的時間點,遇到對的人,不吝提攜並點亮創作的火光。2016年,謝文明正在製作的《夜車》(當時的片名是《我的罪》)陷入了瓶頸,恰巧電影導演楊凡拿著《繼園臺七號》的構想,邀請他擔任動畫導演領導場景設計,「那是一次在電影大師身邊學習練功的難得機會。」後來,謝文明將《夜車》人物塑造、故事情節刻畫與技巧的精進,都歸功於首次的動畫長片經驗,「楊凡導演對美學的要求給了我很多刺激。」
楊凡在這部長片中集合了中港台上百名動畫工作者,先與謝文明在臺灣準備好了完整的劇本和前期設計,接著找遍了臺灣、韓國、日本、泰國的技術團隊,最終才交由北京的青青樹負責製作,以實際人物的動態建立3D模,再繪製為2D動畫。
「他們動畫技術的確很精良,片中一個過氣名伶的角色梅太太身上有件半透明的披肩,需要3D與2D完美結合,動畫團隊也是努力克服製作出來,另外片中的每顆鏡頭都必須用我的素描風格完成,我們在台北設計好、帶去韓國找動畫公司,耗時的手繪素描背景把他們都嚇壞了,最後全靠北京的動畫團隊很有規模地完成。」
紀錄片《逐格造夢》中指出,七○年代,臺灣為美國、日本代工的經驗,培養出首批動畫人才;八○年代成為美國最大動畫代工地,全盛時期,宏廣卡通甚至吃下全球70%的動畫製作訂單,成為當年全球動畫出口量最大的代工製作中心,那是臺灣動畫製作產業的高峰。然而,卓越的代工技術轉成的自製動畫,卻不受市場青睞,讓國產動畫片日漸萎縮。九○年代,更因為動畫製作成本提高,代工產業外移至中國、東南亞,帶走了整批的專業動畫技術人才,讓日後的自製動畫不得不開啟跨國製作模式,比如曾入圍金馬獎的《魔法阿媽》(1998)就是與韓國Plus One Animation動畫公司合作。
《繼園臺七號》的跨國合作經驗,讓謝文明見識到他在臺灣所錯過的整票民間高手的年代,體驗到優秀團隊如何群策群力將作品立體地建構起來,也認知到唯有更妥善、細緻地表現光影、色彩等細節,才能讓作品經得起大螢幕的考驗。
此外,電影長片的故事架構、角色表演的動作刻畫等,都與他過去所使用的短片文體截然不同,而這正是現階段的他所追求的動畫骨幹,「這部長片完成後,我的野心變大了,很想把長片的敘事架構放進短片中,而這是很大的挑戰。」
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《身為職業小說家》中寫道,小説家要能長久堅持創作,可以大致分為「剃刀/柴刀/斧頭」的過程:從初生之犢的聰明鋒利,卻不持久;走到有能力處理較大「木頭」的柴刀期;最終,要能拿得起沈重的斧頭,面對複雜龐大的主題。
這是所有創作者鍛煉技藝的過程,毫無疑問,謝文明讓《夜車》有了顏色、細節、複雜的角色人物關係、頭尾相連的敘事架構,這成就了一整片森林,而他已試著拿起大斧要砍倒巨木。

《夜車 NIGHT BUS》劇照
不跟隨傳統動畫的功夫,只怕時間不夠創作
「我覺得人會恐懼未知的東西,不熟悉的,不了解的,沒看過的。所以在故事編排上,我會安排一些好像沒看過的,或還沒想到的。」謝文明說。這位愛好恐怖、懸疑電影的創作者,削除了故事多餘的贅肉,精煉了動畫的表達語言,用讓人意想不到的方式,將《夜車》塞進了短片這個有限的容器中。
故事從一名孕婦的自白展開,倒敘一起發生在濱海公路夜車上的集體死亡命案。謝文明用兩條主線交錯剪接,放入意想不到的動物角色,用他的說法,那些動物「都很頑強」。他劇透:「其實《夜車》原本沒有猴子的,是一隻山羊,被車撞完就沒戲了,我是因為高雄拍去西子灣田調,才加入猴子的角色,因為猴子讓原本像劇情片的故事多了瘋狂魔幻的劇情。動畫片就是要多點自由,可以做到劇情片沒有的魔幻奇想。」
謝文明將他說故事的靈巧、風格化的表現手法,歸功於短片這種藝術形式所給予的自由,「當代的動畫創作有很多不同的動態詮釋方式。我歷年作品裡的動態都是偏向cut-out animation剪紙動畫風格、需要拆關節來製作動態,很適合恐怖或詭異風格的題材。動畫片裡的所有動態是由動畫導演給予的,可以很自由、很有個人風格。」

謝文明日舞影展獲獎動畫躍上大銀幕,7月8日誠品電影院獨家上映。
「短片是自由的,但若未來有機會做長片,就需要思考如何回收、觀眾群在哪裡,得做更精細的分析。」他朝桌面上擺滿的手稿揮了揮手,「畫這些都是自我開心的!」
他不諱言動畫短片面對臺灣市場的舉步維艱,「在法國,短片非常成功。他們有很專門的製作環境,也有完整的通路。他們不在乎你是短片還是長片,他們在乎藝術,好的藝術。在台灣就現實層面還是需要以長片的市場為第一考量。」
動畫長片確實是這位持續突破自我界線的導演下一個挑戰目標,謝文明召集了臺灣的技術團隊,正在進行的動畫短片《螳螂》,預計在2023年底上映。
「我害怕時間不夠。」十六年過去,謝文明堅持著沒讓自己放棄,阿蛾的孩子平安茁壯了,世界沒有偷走他的夢想,而他正進一步地爭取時間成為他的盟友,「一部動畫電影製作期那麼久,有好多夢想要在時間內完成啊!」他話裡滿溢對創作素樸的愛:「我也期待有天有一部代表自己的長片,但沒關係,先努力讓新的短片達到自己的標準,這比較重要。創作的敵人都是自己的上一部作品。」
(註)王清華,〈1999年中外影片發行與市場概況〉,《中華民國八十九年電影年鑑》,臺北市: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, 1999,頁64-69。




